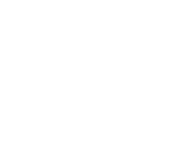撰稿: 新闻与传播学院 易法万
每次触碰这段历史,总会有一种化解不开的凝重萦绕心头。
每次面对这段历史,总会有一种难诉笔端的慷慨荡涤体魄。
这是一段不能忘却的国家历史记忆,它是中华民族陷于危难、荆楚人民抗战自救的见证。
这是一段光荣的的荆楚教育历史记忆,它见证了湖北各界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拼死保住教育、保住荆楚希望之火的拳拳之心。
这是一段不平凡的办学历史记忆,它记录了湖北经济学院的前身——由湖北商业中学堂改名而来的省立“高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顽强生存、延续文脉的历程。
我曾经直接与几位从这段历史中走过来的“高商”学子接触,听他们讲述自己青少年时代在抗日烽火中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的校园故事。我还曾经与两位同事一起,沿着武汉——宜昌——巴东——利川的路线,找寻当年“高商”师生跋涉山川、风栉雨沐的足迹。在湖北商业中学堂创办110年之际,将这段历史纂成一个专题,展现1938—1946年间学校西迁恩施后在巴山蜀水间辗转办学的历史印迹,以志纪念。
日军侵我鄂东 省府断然下令西迁
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后,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2、第11军共约140个大队25万兵力负责对武汉作战,由冈村宁次指挥日军第11军5个半师团沿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2军4个半师团沿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1938年6月15日,日本政府召开会议,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正式决定发动汉口作战。
1938年7月19日,日军从江西九江侵入湖北黄梅县境内;7月下旬进占武穴县境,9月6日占领县城梅川镇。鄂东门户失守,直接危及武汉。
陈诚初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即面对十分严峻的形势。7月,他主持召开了全省公私立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将鄂东、鄂南及武汉地区的中学,分别迁往鄂北、鄂西等地,并将全省47所省立、市立和私立中等以上学校合并为“湖北省联合中等以上学校”,简称“湖北联中”。陈诚亲自兼任校长。
9月下旬,陈诚公开发表了《敬告本省中等学校学生家长书》,说明了举办“湖北联中”的目的和措施,敦促学生家长送子女到鄂西、鄂北联合中学继续学习。他在文告中说道:“这一万多青年真正是我们湖北的精华,最重要的资产。我们一定要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子女,负责抢救出来,好好教育他们。”(台湾《传记文学》1965年第4期)
他还令省教育厅在汉口、襄阳、宜昌三地分设中学生登记处,以便全省l万多名中学生有秩序地迁移,编排到各分校中去。
“湖北联中”校本部设在恩施,分校22所,分布于鄂西、鄂北10个县,学生共13000余人。《中国战时教育》称:“联合中学之设立,有精密之组织计划者首推湖北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教育》,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
“湖北联中”一切经费均由政府供给,学生除免收学费外,食宿、制服以及书籍费均实行政府供给制。当时全国设立“联中”的只有湖北、江苏两省。(后世又有资料表明,抗战时期“湖北联中”在鄂东、鄂北、鄂西共建分校31所,收纳学生3万余人。)
省立“高商”校长张翮接到通知后参加省教育厅紧急会议,受命担任“湖北联中高商分校”校长,负责组织全校师生由武昌西卷棚迁往恩施。
师生汇集宜昌 水路西进遭遇沉船
省教育厅决定将“汉口市直高商”“汉口市商会初商”并入“湖北联中高商分校”,简称“联中高商”,在宜昌集结后西迁巴东县楠木园办学。
学校到达宜昌后,省教育厅又将沙市市职业学校并入联中高商。学校一面派人前往巴东勘查新校址,一面在宜昌接收并入的师生和校产,集结老生,同时还抓住全省学子云集之机招收新生,招聘教师。
1938年11月初,日寇飞机每天对沙市、宜昌两地进行狂轰滥炸。省代主席严立三急电召集联中各分校校长开会,责令即日组织师生撤离宜昌,以保安全。
高商分校当日即组织师生整理装备,撤出宜昌。当时宜昌是全国抗战物资、人员的转运枢纽,一船难求,学校终于租到一艘小型货轮“宝亭”号。
“宝亭”号运载量有限,只能装载校具、图书等物资西运巴东。行至秭归新滩时,水急滩险,“宝亭”号绞曳上滩时翻沉,学校安排的押运人员和几名随行的学生家长不幸遇难,校具、图书全部沉入江中,给后期办学造成严重困难。
师生主力由宜昌乘坐渡船过江。为了避开日军飞机白天的低飞扫射,数百人在苍茫夜色中踏上船板,在长江对岸的安安庙下船。校长张翮亲执灯笼站在渡口照亮,并清点登船人数。来回过渡十余次,全部人马安全过江,在江岸僻静处露天宿营,等待天亮。
第二天拂晓,联中高商师生启程,由陆路向新校址巴东楠木园进发。
历尽千般艰辛 步行抵达楠木园
数百名十几岁的少年,在一群师长的带领之下跋山涉水,踏沟渡壑,整整走了五六天,一路经过宜昌的木桥溪和长阳的高家堰、贺家坪、榔坪,到了巴东野三关才做休整。
在野三关休息三日后,再度启程,折向北行,朝着更陡峭、更荒野的高山进发。学校把人员分为两批,分两天启程。第二批师生动身没多久,就可以发现前一批出发人马的身影,只见他们像一群蚂蚁一般在悬岩绝壁上蠕行。
离开野三关后,第一夜宿营野花坪,次日经绿葱坡宿枣子坪,第三天经茅草荒、杨林荒进入韦家荒。韦家荒这一带,是海拔2000米以上的高山,云雾在头顶弥漫开合,飞机在脚下蜿蜒西航;低头看去,长江如带,轮船如豆。目的地楠木园就在山下江边,屋宇人畜已隐约可见,但师生们还得直下陡坡,走二三个小时,才能到达。
楠木园古镇因盛产楠木而得名,地处巫峡东段,北岸悬崖峭立,南岸是险峻高山,“低头一带水,抬头一线天”就是说的这里。长江流经此处蜿蜒向东,在南岸形成一个曲回的天然港湾,便于泊船,是川江船只进入湖北的第一个栖息港口,也是湖北船只进入四川水域的最后一个歇脚点。因此,川鄂两地的船工都愿意在楠木园停泊歇息。镇上有骡马店、油坊、客栈、茶馆、酒店、商店等40余家,每日人流量在千人以上。
神奇之处在于,20世纪末期考古学家在这里有着惊人的发现。楠木园古镇及其周边留下了古代文明的大量证物。武汉大学考古学余西云教授和他带领的团队据此考证认为,早在7000年前人类就已在三峡地区生活,比距今5000余年的大溪文化还要早2000年。(注: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建成之后,楠木园古镇淹没在江水之中。)
按照省教育厅的安排,湖北联中共有7所分校迁至巴东地区办学,分布在野三关、东瀼口、火峰、罗坪、龙船河等地,高商分校则设在楠木园。师生徒步近半月到达这里时,已是十一月中旬。
受尽苦风凄雨 深根固柢传薪火
联中高商师生在楠木园的艰辛生活并未因为结束了徒步迁徙的旅程而告终。
楠木园这个小镇看似热闹,但流动人口居多,一是过往船只和商旅,二是赶集市的山民。突然一下来了500多人,镇子里首先就没有办法解决住宿问题。学校最终在距江边约三公里的山腰选择了一片开阔地,作为办学场址。
没有宿舍、教室,没有桌椅板凳,没有教具设备……,摆在高商分校师生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困难。校长张翮带领师生自己动手,从山上砍来竹木茅草,建起一座座房舍,制作几百套课桌椅,还有简易的教具,让一群从大都市来的读书人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一直忙乎到1938年12月12日,联中高商才得以正式恢复教学活动。这一天,楠木园古镇上的人们都听得见师生欢腾鼎沸传出的喧闹声。此后若干年,“高商”一直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
对过惯了大城市校园生活的学生里说,更苦的日子还在后面。联中高商非常缺乏基本生活物资,缺米、缺油、缺蔬菜,甚至缺水。学校师生的饮用水、洗漱用水,全都是专人到江边挑回来的,一趟挑一担水需往返数里地。由于生活条件、卫生条件差,疥疮、痢疾、疟疾时有爆发。直到1939年天气变暖之后,学校派人在山间高处找到泉水,用一节节竹筒连接起来,将泉水引到校园里,才算解决了用水问题。
北大黑格尔哲学泰斗张世英教授就是第一批到达楠木园读书的联中高商学生。2009年90高龄的张世英先生回到楠木园寻旧,次年专门写了一篇回忆楠木园生活的文章。他在文中写到:“我们学生宿舍的每间小房里,都是几十个同学共睡在一块用稻草铺的土地上,吃的是稀粥加白薯,晚上几个人共点一盏木子油灯,伴读到深夜。早上一起床就跑几百步石阶,到江边用急流漱洗,然后夹着一本英文书,到山谷里高声朗读。由于当地瘴气重,全校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虱子缠身,疥疮难耐。不少同学因遍体溃烂,听课时只能侧身而坐。比我年岁小的初中一、二年级生,有的疼痛难忍,便一边听课,一边流泪。”(张世英,《张世英回忆录》白发归来思万千,中华书局,2013年11月第1版)
避战祸再迁校 商贸英才成于汪家营
宜昌扼长江三峡东口,素有“川鄂咽喉”之称,自国民政府西迁后,遂成了拱卫陪都的第一道大门。正因如此,1938年10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加紧了西犯重庆的部署,宜昌又成了日军进攻的目标。
1940年6月,日军攻陷宜昌,震惊重庆。宜昌沦陷后,更是成为中日双方争夺的焦点。
设在巴东境内的联中分校虽有三峡天险庇护,但日机飞机时时对巴东县城进行轰炸,安全堪忧。为此,省政府下令巴东境内各分校另觅校址,再次搬迁。联中高商在建始、恩施、利川等地勘察之后,选择利川汪家营为新的校址。
1940年9月,全校师生分两批出发,乘省建设厅轮船“建阳”号经瞿塘峡抵四川万县,然后徒步折返湖北境内,过磨刀溪,越齐岳山,经野茶坝,经月余长途跋涉,到达利川汪家营镇。
汪家营位于川、鄂、陕三省交界处,行政地名为清源乡,是一个高山盆地,四季温暖如春,气候宜人。学校租用了汪家营镇外约二三里远的袁家大屋和苏家大屋,又组织师生搭建了两群茅草房屋充作校舍,赶制教具,以最快速度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校园前临清江,后倚山峦,成为战争年代读书清修的理想之所。
1941年,省政府对教育进行改革,取消联合中学名义,各分校单独设立,联中高商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一高级商业职业学校”,简称“高商”。
抗战西迁时期,学校的专业设置口径比较宽,课程以商科为主,兼顾其他,目的在于培养与商科有关的中等经济管理通才。普通基础课含国文、英语、数学、公民、历史、地理;商业财经理论课,一年级开有经济学、商法、商业常识,二年级开有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合作论,三年级开有保险学、汇兑学。财经技术课,一年级开有商业算术、商业簿记、商业会计,二年级开有银行簿记、银行会计、统计学,三年级开有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
学校十分注意会计制度的更新变动,重视财经技术类教材的更新换代。商业算术、商业簿记、商业会计学、银行会计、统计学、成本会计、政府会计、审计学等课程的教材,几乎全部采用立信会计图书出版社的版本。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教师大多不愿意离开学校,所以师资队伍一直比较稳定。即便如此,学校仍坚持严格选用教师,每学年考核后聘任一次,不重发聘书者视为解聘。这些措施保证了动荡岁月里人才培养的质量。
这个时期的毕业生大体上有三个去向:一是被政府机构录用,这部分学生占比最大,因为当时省政府西迁恩施后缺员严重,而高商学子懂经营管理,正符合政府所需;二是从军报国,有的是报考军校,有的是直接参军;三是升学继续读书,前文提到的北大哲学家张世英先生即为这类代表。张世英从“高商”毕业后,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后曾在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任教,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任教。
抗战胜利后,“高商”于1946年8月迁回武昌,在原校址西卷棚继续办学,校名去掉“第一”两字,全称更为“湖北省立武昌高级商业职业学校”,仍然被人们简称为“高商”。